专家观点
荣新江|谈谈唐长孺先生对敦煌吐鲁番研究的贡献
在2011年中华书局在北京举办《唐长孺文集》出版座谈会上,我曾经说过,唐先生(1911-1994)不仅仅属于武汉大学,唐先生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者,是一代宗师。我作为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一名史学研究者,也一直在跟踪阅读学习唐先生的论文和著作,幸运的是1983年曾经在避暑山庄里,参加《大百科全书·隋唐》分册的审稿会,等于听唐先生讲课。对于唐先生所撰的敦煌吐鲁番学方面的论文,几乎每出一篇,就马上拜读,以后在处理相关问题时,还会反复阅读理会。今天我们在武汉大学纪念唐长孺先生诞辰110周年,我就重点谈谈唐先生对敦煌吐鲁番研究的贡献。
一、
早期的敦煌文书研究
唐先生和许多老一辈学者一样,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为根基的,但对于新材料非常敏感。唐先生以《唐书兵志笺证》名家,其实就在写作《兵志笺证》的同时,唐先生已经关注敦煌文书中的唐朝新史料,他撰写的《敦煌所出郡姓残叶题记》一文,发表于1948年3月14日的《武汉日报》上(收入《山居丛稿续编》)。这段时间里,唐先生还撰写过一篇《白衣天子试释》(《燕京学报》第35期,1948年),利用王重民先生等发表的金山国张承奉的资料,推测白衣天子与摩尼教有关。唐先生早前治蒙元史,关心塞外史地和中西交通,故有此论。
然而,早年中国学者限于条件,英法所藏的资料不易见到,只能就学者们发表出来的材料加以论说。当1957年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过日本东洋文库交换得到英国图书馆所藏的S.1-6980号写本缩微胶卷,中国学者才得以浏览英藏敦煌文书的整体面貌。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始的图像材料在中国并没有像在日本那样引起足够的重视,真正从历史研究角度利用这批资料的,主要就是唐长孺先生。他撰写了《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从缩微胶卷中首次录出一些重要的文书,如《沙州进奏院状》等,对归义军史、特别是张氏归义军有精辟的考证,大大推进了归义军史的研究(1962年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他又撰写了《敦煌所出唐代法律文书两种跋》,是对S.1344和S.4673两件法律文书的考释(1964年6月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此文最后说“我于1957年在科学院图书馆抄录斯坦因盗窃去的敦煌资料(胶卷)”,可见唐先生捕捉新材料的眼光和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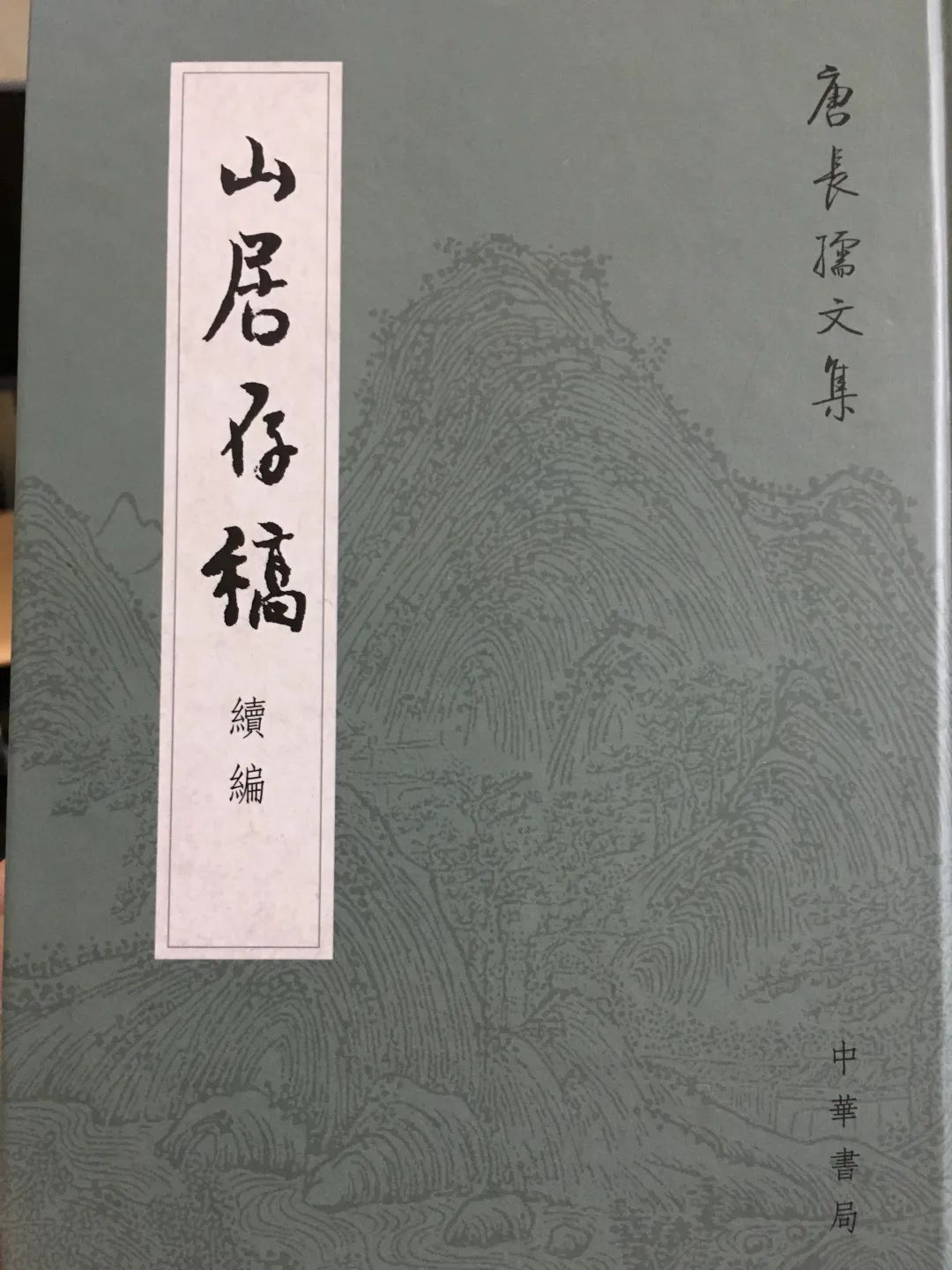

唐长孺先生著作
二、
解放后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
与英藏敦煌文书的利用相比,唐先生对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更大的贡献是对解放后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利用。从1959年到1975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喇和卓两个墓地曾进行过13次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纸本文书,在陆续发表的考古简报中都有报道,但并没有学者想到应当集中整理。70年代中期,唐先生意识到这些文书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向国家文物局领导报告这项工作的意义,并亲自与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一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把所有出土文书全部调到北京,成立了以唐先生为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经过数年的努力,从1981年开始出版平装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到1991年出版了10册;此后1992-1996年又出版了图文对照本四大册;囊括了所有当时已经初步整理出来的吐鲁番文书,做出了精准的定名和录文。这部著作为中古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提供了全新的资料,特别对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也在此前大谷文书、斯坦因文书、黄文弼文书的基础上,发表了大量此前未见的新材料。唐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四巨册,可以说是吐鲁番文书整理史上的里程碑,影响极其深远。我后来主持《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完全是亦步亦趋地按照唐先生订立的规范来做,如果没有唐先生确定的整理文书的规范,这一规范大大推动了此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也给后人的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确定了标尺。
唐先生本人身体力行,在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中,也贡献至多,先后发表《吐鲁番文书中所见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1978年第6期),《吐鲁番文书中所见高昌郡军事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和传播》(《出土文献研究》,1985年),《唐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问题》《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唐西州差兵文书跋》(以上三文刊《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唐先天二年(713)西州军事文书跋》《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西州府兵》(以上两文刊《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唐肃代期间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等文章。这些文章所涉及的时段从高昌郡,经西州,到安史之乱后西州的最后年代;涉及的内容包括行政、军事制度,均田制、籍帐和丁中制度,还有唐先生最为熟悉的唐朝兵志,以及丝织技术的传播问题,都是吐鲁番史及中古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贡献良多。唐先生还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1990年)等论集,发表整理小组成员有关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的论文,整体上推进了我国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水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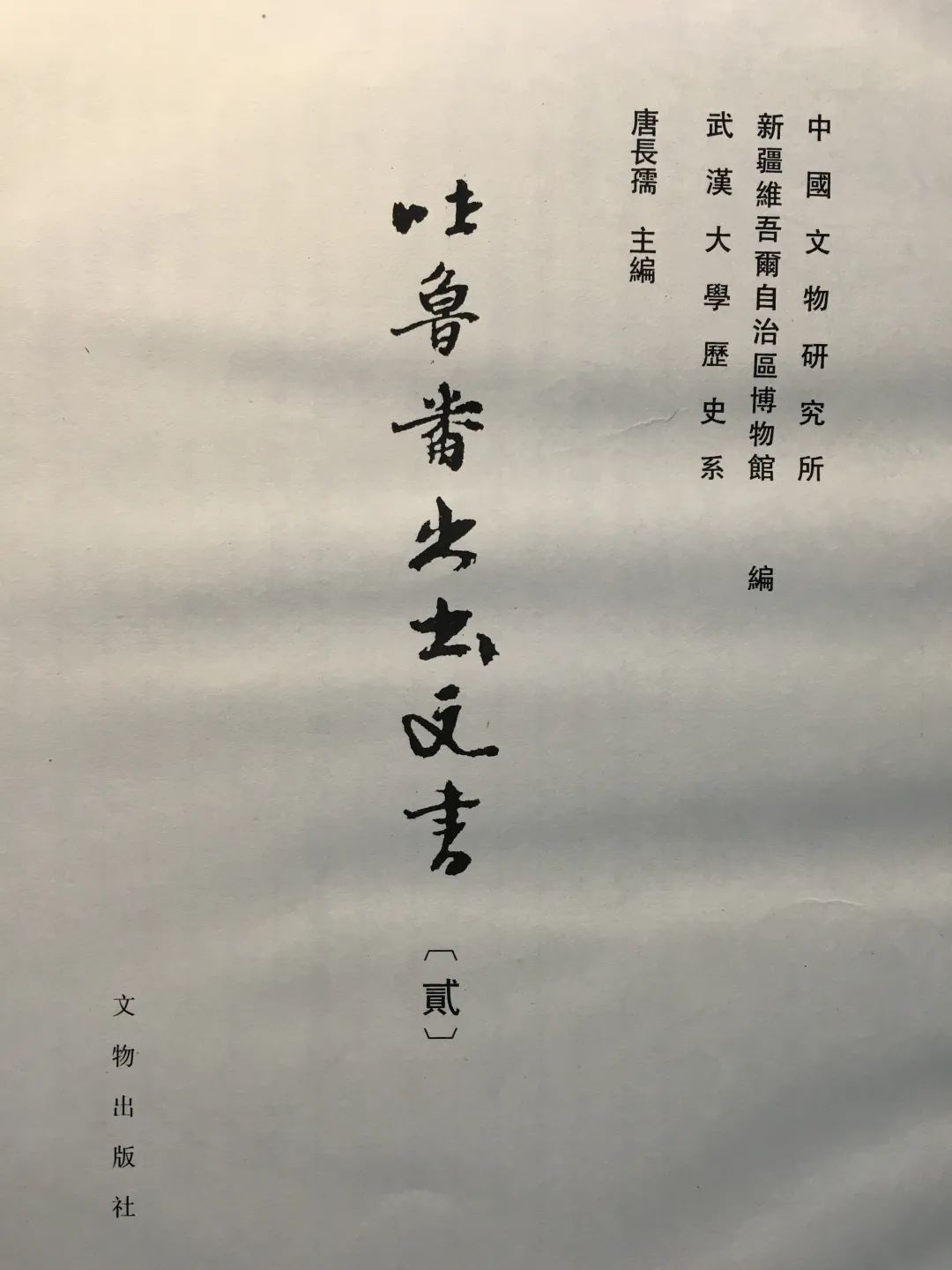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
三、
对敦煌吐鲁番学科建设的贡献
从20世纪初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开创中国敦煌学研究之始,虽然也注意到了吐鲁番出土的文献、碑刻和绘画,罗振玉整理过吐鲁番出土的碑志,王仁俊也留意过《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但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一直是敦煌的附庸,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一直以敦煌文献和石窟图像为主体,吐鲁番资料作为补充。
1980年代初,北京的学者在酝酿全国性的敦煌学会,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在积极筹备全国性的敦煌学术研讨会。当时在北京的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持吐鲁番文书整理工作的唐长孺先生,积极努力推动,使得最后在1983年成立的学会,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名字出现,我想把吐鲁番包含在内,是唐先生的贡献。而这一点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问题,而是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学科建设的巨大贡献。从此之后,吐鲁番的研究与敦煌学比翼齐飞,任何敦煌学的研究中都离不开吐鲁番的资料和成果了。

唐长孺先生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整理吐鲁番文书,1980年摄于北京沙滩红楼
四、
典范的意义
最后再谈点自己在学习唐先生论著中的一些感想,特别是在方法论方面对我的启发。
一是唐先生在处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时,首先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并用当地行用的中原制度来解释相关的文句。比如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中“去歲官崇驄馬政,今秋寵遇拜貂蟬”一句,过去的理解有误,唐先生正确地指出“貂蟬”指的是加散騎常侍,于是各种史料之间就没有隔阂了。这一点对我启发很大,所以我在做归义军史研究时,首先全盘整理敦煌文书中归义军节度使的加官问题,解释了所有节度使的“称号”,才能是大量文书放在合理的年份中去说明问题,否则就很容易弄错。
二是做研究要先做史事编年。唐先生在开始发表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时候,是从高昌郡的行政和军事制度开始的,他几乎同时发表的《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从楼兰出土简牍中搜寻早期的高昌史料,表明他是从头梳理高昌史料的。更具代表性的一篇文章是《高昌郡纪年》,发表在当时还是内部刊物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期(1981年3月),按年份辑录《十六国春秋》等史籍、文书中的高昌及相关的河西、中原史事。唐先生一直没有正式发表这篇文章,也没有收入他自己编的《山居丛稿》,说明他不是把它当做正式的研究成果,但却对初学者有很大的帮助,我在处理高昌郡时期的历史时,一直依赖于这个《纪年》,也在页边(后来在电脑里)做了一些增补。这个《纪年》告诉我们,在研究一组哪怕是非常偏远的课题时,先要做出相关史事和资料的编年工作,这是其他研究论文的基础。
三是唐先生在整理研究这些西北出土的残片断简时,胸中一直有着对中国历史大问题的关怀。1995年我接受办《唐研究》,首先最想约到的是唐先生的稿子,通过唐门弟子的帮忙,唐先生的《跋吐鲁番所出千字文》成为《唐研究》第1卷的压卷之作(1995年12月出版),这篇文章虽然写的是吐鲁番文书中本来很不起眼的《千字文》,大多是学生的习字,但唐先生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从西州《千字文》的习字,阐发出从北朝后期,“南朝文化包括学术思想、文艺对北方日益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这是历史的潮流”这样宏大的叙事,这是和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一脉相承的。
回到我发言开始的话,唐先生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一代宗师。美国丁爱博教授在编辑《早期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这本会议论文集时,一定要收一篇中国大陆学者的文章,这就是唐先生的文章,虽然唐先生没有参加这次在海外举行的研讨会(Dien, Albert E.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1980-1981年,唐先生应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邀请,赴京都访问,发表一系列讲演,其中的《新出吐鲁番文书简介》发表在1982年京都大学人文研的所刊《东方学报》第54册上;他的另一篇讲演稿,发表在《东方学》上。1983年8月31日—9月7日,唐先生再次前往日本参加“第31届亚非人文科学大会”,发表“A Study on Local Census Registers 诸乡户口帐 in Hsichow of T’ang Dynasty Found in Turfan”一文,英文摘要发表在会议纪要(Proceedings)第2册999-1000页。这些文章和摘要虽然不多,但在“文革”之后中国学术界刚刚开始敞开国门的初期阶段,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学术史上值得重视的。
唐先生这一代学者,为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确定了标准和规范,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留给我们丰富的学术遗产,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2021年7月18日在纪念唐长孺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